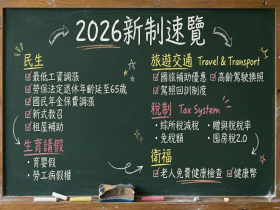我回想起馬拉威人,記憶中只有正直、溫暖和單純,那是一套無法用數字估量的特質,卻更加可貴。馬拉威人對於一蹶不振的政經現狀也很無奈,但他們並不會因此走歪路剝削觀光客。
在這趟四個多月的非洲之旅中,馬拉威始終在我心中佔有一塊柔軟之地。馬拉威素有「非洲的溫暖之心」(Warm heart of Africa)的美譽,以前我總覺得「美譽」是言過其實,什麼小瑞士、東方威尼斯、香格里拉、皇冠上的明珠,帶著鄉野傳奇的渲染的成份,但是,馬拉威的溫暖人情,真切是我這趟旅行一個美好的逗點,終於我上路不必像打仗,接受幫助不必心懷疑懼,山是山、水是水,從來沒有暗藏弦外之音。
曾經在里翁代(Liwonde)某個營地,我滿懷歉意看著黑人經理提姆幫我修理夾腳拖。提姆天生有種高貴的氣息,看到他讓人不自覺把背脊挺直,舉止放優雅,說話避免任何F措詞。我只是隨口問他有無黏膠可借我修鞋,他便逕自把我鞋取走,坐下來專注仔細修理著我那雙破爛夾腳拖,像瑞士錶匠在處理陀飛輪一樣謹慎。我赤著雙腳,身體歪歪斜斜支撐在老闆打造的圓木板凳上,跟周遭蠻荒氣息十分匹配。我頭上垂下來一大堆電線,是大家趁還有日光時搶些太陽能充電用的,趁他專注之際,我跟懶貓一樣趴在桌上問他:「提姆,我來馬拉威已經兩週了,發現你們人真的很善良。到底為什麼?」
提姆不急不徐說:「因為我們以前有位總統,他倡導國民要遵守仁愛、溫和、禮貌,我們馬拉威人相信只要你待人以禮,日後好運也會回到身上來。」雖然我事後查了又查,自1966 年馬拉威脫離英國成為共和國以來,總統不是獨裁二、三十年,就是貪腐醜聞纏身,拖拖拉拉到目前也才第五任,似乎沒有一個可以扛得起他口中那勤政愛民形象的代表,但是我喜歡他那彷彿描述童話故事的口氣。
有時候想來很奇妙,到底是什麼因素,可以主宰一個國家的民情。這是DNA先天決定,還是政治後天養成?是人類學的範疇,還是心理學可以分析?
事後,我常常想起這段隨意的對話,以及在傍晚,周圍傳伴隨土狼笑聲而來的荒野氣息。嚴格講起來,馬拉威並沒有我們刻板印象中非洲固有的壯闊原始,無論莽原如何蔓延,其中有道山谷帶著蓊綠溫柔氣息;河馬家族怒氣沖沖在河裡洗澡,不遠的地方總有小孩嬉鬧波濺水花;就算千辛萬苦爬到穆蘭吉山頂(Mulanje),還是有個駐守山上、笑盈盈的管理員,為你劈好柴讓你煮飯取暖,只為賺取微薄小費;就連來趟獵遊,也是價格親人、服務周到,看看大象、羚羊等跑龍套等級的動物,小確幸到極點卻也很讓人舒暢。
而奇妙的是,這一切在莫三比克邊界便已出現端倪。是因為喝多了馬拉威的水嗎?邊界的莫三比克人格外溫和,我、愛爾蘭妹綺拉、加拿大阿宅凱文,三個像大象伸長鼻子嗅到湖泊的水氣一樣,感受到民風驟變。從莫國跨到馬拉威過程非常漫長而有趣,經過辛苦漫長的公車轉小巴以後,我們灰頭土臉來到邊境小鎮,一個小矮子從一堆腳踏車中殺出重圍朝我們衝來,有點害羞說:「我,卡夏,記得我,你們明天,跟我訂腳踏車,去馬拉威。」
原來,從這裡到邊境關卡有段距離,他們解決的方法是「單車Taxi」,你跳上他們破爛腳踏車的後座,以大約台幣兩百的價格,讓他們載你到移民辦公室。
於是當晚我們訂了三輛單車Taxi,讓卡夏和他兩個朋友都受惠,大家今晚也都能有個好眠。卡夏怕別的司機魚目混珠,還扯扯身上的外套跟我說:「記得,我的紅外套,明天早上六點,我,外面等。」不得不說這招還真睿智,沒有他提醒,隔天我們可能輕易就被另外三個黑人給迷糊載走。
第二天清早六點,一開門便看到三個高矮不同身影牽著單車在外頭等待,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件顯眼的紅外套。「卡夏,六點等。」他咧嘴微笑,當他知道自己載的是小個子愛爾蘭辣妹時,嘴咧得更開了。於是我們三個就這樣歪歪斜斜出發,儘管輪胎無氣有力,馬路赤裸崎嶇,有了非洲強勁鳥仔腿的踩踏,一路仍算平順。我們迎著早晨的風,使力挺著快被肩上背包折斷的腰椎,欣賞著紅土路旁無數泥屋、早起工作的媽媽,和派對到清晨的年輕人。沒錯,早上六點,泥屋前擺一台老收音機放著非洲舞曲,一群人歪歪倒倒跳著舞,蔚為奇觀。
「妳好,妳是台灣來的,我看妳護照就知道,我們兩國以前是好朋友。」2008 年初,馬拉威新聞部長帕特里夏卡利亞蒂(Patricia Kaliati)將馬台四十二年的邦交關係比作「失敗的婚姻」。「我們渴望發展,可是台灣給馬拉威所帶來的變化卻太少太少。」她曾感慨地說。儘管當時這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,卻是可理解的。比起中國以灑錢或投入大量勞工方式為非洲國家帶來顯著建設,走小巧精緻搏感情路線的台灣,的確相形見絀。不過,夫妻分手後仍當成朋友,至少簽證官對我格外親切。
「妳手肘上那一塊紅紅點狀斑是什麼東西?」他問我。
「喔,我也不知道,已經好一陣子了,不痛不癢,應該沒事啦。」
「這裡畢竟是非洲,妳要趕快去看醫生哪。喔對了,妳不能拿落地簽證。」
正當我還陶醉在被移民官呼呼的喜悅中,他卻突然送我當頭棒喝。「但是……但是,我查了好久,網路上說可以在邊境領簽證啊!怎麼會這樣?」其實關於馬拉威簽證的取得,各方資訊非常曖昧不明,非洲的簽證規定總是這樣的,沒一天說得準。
「喔,我們最近改了。但沒關係,我給妳七天緩衝時間,妳入境後,看是要去南方的布蘭泰(Blantyre)或是中部的里朗威(Lilongwe)移民局辦簽證就好。祝妳一路順風!」我不敢置信,他就這樣輕易放過我,換成在莫三比克,肯定不是會被狠狠噱一頓,就是要重新跳上兩天兩夜的恐怖公車回首都辦理才行。
「對了,妳留個E-mail 給我吧,我一直想去台灣,以後去台北找妳。」雖然他來台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但我哪敢不從。後來我才發現,跟台灣人要E-mail 並相約台北見,在馬拉威是股風潮。
我沿路共跟四、五個路人交換E-mail 並相約台北見,還在回台某一天收到一則Whatsapp:「嗨,妳好嗎?」「請問你是……?」「我是馬拉威邊境官馬克啦,等下供電就要斷了,先跟妳打個招呼喔>.<。」
關於「尋夢」與「被寄生」
在現實生活中,我們設想一套評鑑標準來判斷一個國家的水平,例如愛滋病罹患率、識字率、失業率和國民生產所得等,就這一點,馬拉威常常被打趴。
但是,在貧窮很容易和「卑微」「奸巧」或「鋌而走險」沾上邊的同時,每回我想起馬拉威人,記憶中只有正直、溫暖和單純,那是一套無法用數字估量的特質,卻更加可貴。馬拉威人對於一蹶不振的政經現狀也很無奈,但他們並不會因此走歪路剝削觀光客,比較像「好吧,有朋自遠方來,大家交個朋友,看以後有沒有機會我也雞犬升天一下!」的心態,不是最聰明,卻讓旅人們可以鬆口氣。
我和綺拉從莫三比克島便投緣起來,一路熬過辛苦的搶票行程、漫長火車、超擠小巴、混亂邊境,像打了一場兵荒馬亂的仗以後,終於抵達馬拉威湖南端的麥卡萊角(Cape Mclear)。對習慣一個人旅行的我來說,旅行中的牽牽絆絆是太無謂的累贅,即便和老公出門,上限也只有兩星期,若能在旅途中遇到好伴,可謂天賜良緣,但若遇不到,我也是自得其樂界的達人。
曾看過一段話,大意是說旅行會為你帶來世界觀,卻也限制了你專注在一事一物、此時此刻的能力。你心裡總惦記著的有更多路要走、更多風景要看、更多人要遇,因此當下的一切,就算稍縱即過也沒啥好留念。或許是這種「可拋棄式」,讓旅行和現實生活一分為二,多了迷人色彩,也常讓旅人們深感「回不去了」,尤其是旅行好長一陣子的人,往往被抽離現實感。
我從二十一歲開始旅行到現在,經常在這兩者間往返、摸索、掙扎、思索,始終沒有答案,但我始終認為,只要同時具備在兩者間「穿梭、切換」的能力,就沒什麼好擔心。只是,這趟非洲之旅,隱約有種指標性意義,在我決定全然獻身家庭之前,它是否是趟謝幕之作?
綺拉也有相同的思索,她在都柏林從事電影業,聽起來像執行製作之類的職稱,總之,在片場發生的大小事,都要靠她來協調。她當過茱麗葉畢諾許的私人助理,也和某超級英雄男演員短暫交往過(她一再要我發誓不能說出名字),有著愛爾蘭人天生的雀躍、幽默、機智、灑脫和嗜酒如命,像男孩一樣直爽,又跟女孩一樣纖細。一路上,我們永遠不必擔心沒話題聊,不論在什麼痛苦的交通工具或斷水的旅館,我們倆永遠可以手拿一杯啤酒,跟阿珠阿花一樣笑到掉眼淚。同樣也是資深旅人的她,來過非洲很多趟,而這一趟最重要的使命,就是「尋找事業轉換跑道」。
「我想看看有沒有機會,在保護區工作,我真的很喜歡非洲,希望可以在這裡度過下半生。」綺拉今年三十七歲,過往戀情豐富,卻始終遇不到Mr. Right,感覺上她已經放棄那條路,只想有個自己的小孩,在非洲好好把他扶養長大。
我想像一個三十七歲的漂亮女人,在都柏林的夜裡踩著高跟鞋寂寞走回家,不是因為釣不到男人,而是因為太知道戀愛其實就是那麼回事,所以無法忘情投入,畢竟,一旦在愛情裡失去自己,就像在非洲莽原迷路一樣危險吧。
在平靜的麥卡萊角,我們喝著久違的香濃咖啡(也是馬拉威特產之一,Mzuzu Coffee),感覺自己重新當回像樣的人。白天,我們沿著馬拉威湖散步,腳邊伴著傻頭傻腦的雞、鴨,看村民在湖邊洗著鍋碗瓢盆和髒衣服;有時候雇一艘獨木舟和船夫,罔顧湖裡有肝吸蟲(Bilharzia)的傳說,到不遠的外島去游泳、浮潛、曬太陽、喝啤酒。遇上了辛巴威來的幾個年輕白人農夫,我們倆個躲在房裡以克難化妝品梳妝打扮一番隆重登場,然後我會為綺拉適時展現的女性魅力驚嘆不已。她可以聊魚苗培育、農業發展、NGO 現況和肝吸蟲,說的時候那雙綠色眼睛閃爍著光彩。到了晚上,我們會換上洋裝,到村裡某間像樣的餐廳,開一瓶紅酒喝到微醺,然後在月光下散步回旅館。
曾經臉書流行過一篇文章,意思是千萬不要愛上愛旅行的女孩,我想綺拉就是箇中代表。其實,我必須要為女孩們說說話,不是不要愛上,只是你要有寬闊的胸襟和很大的能耐而已。〈本文選自第4章,曾琳之 整理〉
我從二十一歲開始旅行到現在,經常在這兩者間往返、摸索、掙扎、思索,始終沒有答案,但我始終認為,只要同時具備在兩者間「穿梭、切換」的能力,就沒什麼好擔心。只是,這趟非洲之旅,隱約有種指標性意義,在我決定全然獻身家庭之前,它是否是趟謝幕之作?
綺拉也有相同的思索,她在都柏林從事電影業,聽起來像執行製作之類的職稱,總之,在片場發生的大小事,都要靠她來協調。她當過茱麗葉畢諾許的私人助理,也和某超級英雄男演員短暫交往過(她一再要我發誓不能說出名字),有著愛爾蘭人天生的雀躍、幽默、機智、灑脫和嗜酒如命,像男孩一樣直爽,又跟女孩一樣纖細。一路上,我們永遠不必擔心沒話題聊,不論在什麼痛苦的交通工具或斷水的旅館,我們倆永遠可以手拿一杯啤酒,跟阿珠阿花一樣笑到掉眼淚。同樣也是資深旅人的她,來過非洲很多趟,而這一趟最重要的使命,就是「尋找事業轉換跑道」。
「我想看看有沒有機會,在保護區工作,我真的很喜歡非洲,希望可以在這裡度過下半生。」綺拉今年三十七歲,過往戀情豐富,卻始終遇不到Mr. Right,感覺上她已經放棄那條路,只想有個自己的小孩,在非洲好好把他扶養長大。
我想像一個三十七歲的漂亮女人,在都柏林的夜裡踩著高跟鞋寂寞走回家,不是因為釣不到男人,而是因為太知道戀愛其實就是那麼回事,所以無法忘情投入,畢竟,一旦在愛情裡失去自己,就像在非洲莽原迷路一樣危險吧。
在平靜的麥卡萊角,我們喝著久違的香濃咖啡(也是馬拉威特產之一,Mzuzu Coffee),感覺自己重新當回像樣的人。白天,我們沿著馬拉威湖散步,腳邊伴著傻頭傻腦的雞、鴨,看村民在湖邊洗著鍋碗瓢盆和髒衣服;有時候雇一艘獨木舟和船夫,罔顧湖裡有肝吸蟲(Bilharzia)的傳說,到不遠的外島去游泳、浮潛、曬太陽、喝啤酒。遇上了辛巴威來的幾個年輕白人農夫,我們倆個躲在房裡以克難化妝品梳妝打扮一番隆重登場,然後我會為綺拉適時展現的女性魅力驚嘆不已。她可以聊魚苗培育、農業發展、NGO 現況和肝吸蟲,說的時候那雙綠色眼睛閃爍著光彩。到了晚上,我們會換上洋裝,到村裡某間像樣的餐廳,開一瓶紅酒喝到微醺,然後在月光下散步回旅館。
曾經臉書流行過一篇文章,意思是千萬不要愛上愛旅行的女孩,我想綺拉就是箇中代表。其實,我必須要為女孩們說說話,不是不要愛上,只是你要有寬闊的胸襟和很大的能耐而已。〈本文選自第4章,曾琳之 整理〉
作者:李郁淳
射手座,六年級後段班。曾任《哈潑》、《美麗佳人》、《bella儂濃》等女性時尚雜誌採訪編輯,也曾為Elle、FHM、Yahoo奇摩等媒體撰寫旅遊文,因而培養出華麗虛幻的文風,唯有旅行時才覺得自己慈眉善目、胸襟廣闊。堅持一個人旅行,足跡遍佈各大洲四十多國,最常和在地人把酒言歡,也不排除偶爾被惹毛暴走的可能。認為人和自然是旅途中最美的風景,遇到教堂、廟宇和博物館會開始微放空。擅長插科打諢,跑步玩狗,天生有著老靈魂,多數時候卻不想長大。
什麼,你問我旅行的意義?背起背包出發就是了,別說那麼多。
粉絲頁:漂鳥旅行誌(Birdy’s Migration)
email:birdism@yahoo.com
出版:啟動文化/大雁出版基地

書名:想入非非:一個人的東非130天大縱走
目錄:
一、馬達加斯加:最純粹的荒野與多文化交融
二、南非、史瓦濟蘭:小南非,黑台灣
三、莫三比克:美麗海岸背後的原始獸性,葡萄牙殖民、內戰、共產主義交替產生的噬血性格
四、馬拉威:台灣的好朋友,非洲的溫暖之心
五、坦尚尼亞:高山與平原,觀光業對當地帶來的變相衝擊
六、盧安達、烏干達:強烈對比的鄰居
七、肯亞、衣索比亞:驕傲得令人不知所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