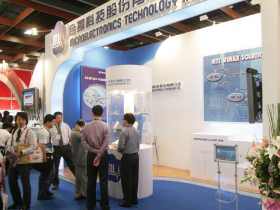王偉忠的新作「光陰的故事」,彷彿是一張用歲月編織而成的心網,讓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、亞都集團總裁嚴長壽談起兒時記憶,話匣子一開,就順著回憶的長河流下去……
「春天的花開,秋天的風,以及冬天的落陽,憂鬱的青春,年少的我,曾經無知的這麼想……。」談著近來收視開紅盤的新作「光陰的故事」,「電視鬼才」王偉忠不禁哼起這首深植在他腦海裡的小調。對於王偉忠而言,製作這類的故事,就好像是替自己,以及同樣身為四、五年級生的觀眾,把過往年少的歲月,重新溫習一遍。
「做節目很像撒一張網,網進很多觀眾的共鳴;也很像辦桌,放了很多桌子,擺上了菜單,只要很多人來,就很開心。」這回,王偉忠不僅讓自己沉浸在舊時的記憶裡,許多企業老闆和名人也上鉤了,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、亞都集團總裁嚴長壽談起兒時記憶,話匣子一開,回憶就順著歲月的長河,流著流著……。
第一幕 代工天王郭台銘…
我是在埔墘長大的,那時候板橋跟台北市就是一座光復橋連起來。小時候是跟著外婆住,我不是在眷村長大,而是在本省人的社區裡面長大。可是我外婆不會講台灣話,只會講山東話、煙台話;所以,我第一個會講的是外婆的山東話,第二個會講的是台灣話;等入了小學,才開始學ㄅㄆㄇㄈ,國語是我的第三種語言。
那時,我回家講的是山東話、煙台話,出去外面跟朋友玩,就講台灣話。每次外婆去買東西都會帶我去做翻譯,甚至還靠我的台灣話跟賣菜的殺價。有時候殺價成功,外婆就會給我兩三毛的零用錢,那時會覺得自己立了好大的功勞。
我是埔墘國小的第一屆學生,那時候,學校根本不是學校,只是借了一個像是里民代表大會的禮堂上課,只能坐幾十個人,埔墘國小就從那裡開始。等到我父親的工作調回板橋,我就轉到板橋國小去了。
老師打學生,天經地義…
在那個時候,日本式的傳統教育觀念很重,還沒有太大的改變,所以老師都是非常嚴厲,很踏實、認真、用心地在教我們。每一個班的老師都有籐條,還有木板,如果題目答不對,或者作業沒有寫好,老師就會問說你要籐條還是要木板,我們可以自己挑。
雖然是被打,但那時覺得老師打我們,是天經地義的。當然,老師都是打手掌,或者打屁股,不會打到傷到你的筋骨。如果自己能夠一個禮拜不被打,那已經是很幸運的了。
我們認為老師打我們都是愛護我們的,都是來教育我們向善、把工作和功課做到最好;不會有任何人想說:唉呀,老師你打我們,我們家長會去怎麼樣……我想我們都沒有這種觀念,那時我們都非常尊敬老師。如果,叫我們罰站十五分鐘,老師不叫我們走,我們絕對不敢離開。
還有,就是快要五、六年級的時候,同學說附近有座教堂,只要禮拜天早上跟著他們去唱唱聖歌、聖詩,坐幾個鐘頭,累積幾次以後,就會發給你一包麵粉,累積幾次,就發一些奶粉給你。
一本漫畫書,全班傳閱…
我們家裡是信佛教的,但教堂並沒有規定你一定要信教才能去,所以我就去了幾次,累積了幾個月的成績,我記得第一次拿了幾瓶奶粉和一袋麵粉回去,媽媽很高興。後來麵粉吃完了,媽媽就用麵粉袋給我們做成內褲,小時候就穿著這種上面印有中美國旗、外面買不到的內褲到處去玩。
雖然,過去那個年代物質很貧乏,可是精神一點都不貧乏。有任何好東西也都會拿出來彼此分享,有時候誰去買了一本好的漫畫書,就會拿到學校供全班傳閱。
例如,那時候,我們還有葉宏甲、大嬸婆等,每次看完葉宏甲,都急著想看下一集,但總要等一兩個禮拜才出一本,大家就輪流去租,有時候,五、六位同學湊錢,可以去租一個小時,那一個小時裡,大家擠在一起看,看那個大戰鐵面人的結局是怎樣。
搬磚塊防洪,不分省籍…
那時,我們家周邊都是田埂,都是本地人,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感覺到說你是外省人啦、本省人的。大家有什麼困難,都彼此幫忙;比如說淹水,那時候排水系統不好,大家就幫忙去搬磚塊、釘木頭,把門口進水的地方擋起來;彼此都互相扶持,不會想到你是來自哪裡、我們又是來自哪裡。
這些都是我們現在看不到的現象,隨著物質生活富裕,大家看到的都是這個社會比較負面的東西,沒有看到人性單純和善良的一面。我現在回憶起來,比較想念台灣過去那種單純、和善、尊重倫理的共同價值觀。
第二幕 飯店業教父嚴長壽…
我是三十六年次的,民國四十幾年開始上學,那是一個非常貧苦的環境。
就像一位作家形容詩人葉慈的故鄉愛爾蘭:「那個時代這地方貧窮是一個事實,既不感覺不光彩,也不覺得羞恥」。我們那個時代,就是這樣一個環境,大家都很窮,都在一個很擁擠的環境裡面生存,但一點也不覺得羞恥,不過,也不會覺得不光彩。
我的幾位哥哥,在十四、五歲的時候,都已經到外面去做學徒了。家裡沒有太多能力,我父親也覺得就學一技之長吧;所以,我幾位哥哥分別在機械工廠、印刷工廠、麻繩工廠和麻籃工廠工作,他們就這樣從學徒開始做起,到後來也都為自己開創了一片天空。
為了補習,新店騎到中山堂
我對幾位哥哥都是非常佩服的,他們比我更早接觸到困苦的環境,都是在非常小的時候,就要忍受辛苦,除了要努力自己找機會讀書學習,還要想辦法拿錢回家。
我記得,我大哥在新店的中華彩色工作時,那時我家住在新莊,他下班後要到中山堂附近補習,一路都是用腳踏車來做交通工具,可以想像他光是這件事就花多少時間。這麼辛苦就是要讓自己更好,那真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。
我自己當兵回來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美國運通做傳達。那時候是一九七一年,正好遇上台灣退出聯合國,作為一個連自己的生活都照顧不好的平凡年輕人,我卻也強烈感覺到自己像是世界孤兒。
練好英文,讓外國人看得起
但在美國運通工作的時候,我才發現居然還是有許多外國人來台灣,他們把美國運通作為通信處,我們幫他們收集信,然後他們拿護照來領取。
我當時就發現,如果能夠把我的英文練好一點,我的服務就可以讓這些客人更感動;其實,我那時的念頭已經超越了想要賺錢,或是得到人家的讚賞,我甚至覺得我好像某種程度上是在為自己的國家做一點事。
那時候,就是像我一個這麼卑微的角色,都有那種希望台灣被人家看到、要人家看得起我們的好強心理。
其實,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壓力,現在台灣社會裡的年輕人,壓力不見得比我們那時小。
當時,只要你努力,你就有機會出人頭地,或者至少有一個非常安定的工作,讓自己有生存的機會。
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更徬徨,因為每一個人出社會都有大學學歷,但其中有些人還是會被分配到去做很基層的工作;而當你面對這種基層的工作時,你心情的調適會更加困難。
表達感謝,幫朋友煮飯燒菜
此外,我感受比較深的是人與人的關係。我覺得,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表達感情的方法,而且非常直接。
當時,我家搬到台北,我母親的一位朋友在南部生小孩,我母親報答她的方式就是去那邊幫她坐月子;印象中,我母親去住了一個月,目的等於是幫她家煮飯燒菜。那時候,大家都用自己最原始的條件,去表達對別人的一種感情或是關懷。
那真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代,台灣已經走過了,但是,同樣的,在那個年代,那種人與人之間非常近距離的感情,也相對變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