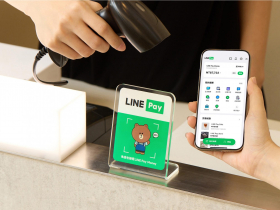《年少日記》是電影裡少年的日記,也是香港導演卓亦謙對憂鬱反思的日記,同時,他更用這部作品,擁抱所有被壓抑、受傷的靈魂。
金馬獎頒獎的這一整天,卓亦謙的神經快節奏地張弛,一會兒有些緊張,一下子又亢奮了起來。
時間過得很快,倏地就到了深夜兩點多鐘,周圍慶功的氣氛仍在鬧騰,他抿了幾口白酒,掏了根菸,帶著他的粉紅色河馬:一隻皮毛已經有點痕跡的胖玩偶,和女友Genie緩緩走出了餐廳。
來自香港的阿卓,是《年少日記》的導演,今年他靠著這部電影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和觀眾票選獎。鎮日折騰,身子已有倦意,他清瘦的手腕幾乎拿不太動超過3公斤的金馬獎座了,但卓亦謙眼神裡頭的光火未熄,始終藏著一些纖細敏感、一些抑鬱、一些脆弱,和一些不可名狀卻非常熱切的東西。
他的作品《年少日記》,也像他的眼神,像首憂鬱卻不張揚的詩。

初衷》喪友之痛 讓他對生命不斷反芻
戲中由一本孩子的日記串連起雙線,一廂,小朋友鄭有傑賣力想讀好書、彈好鋼琴。但他總是比不過優秀的弟弟,而精英父親病態的完美主義,和他鞭打兒子的雞毛撢子,冰冷分數和家人失望目光,都讓鄭有傑「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」這個夢想愈來愈遠。
另一廂,長大成人的年輕教師,發現自己班上同學寫的遺書,少年隨時可能步上窄仄階梯,爬往天台,再一躍而下⋯⋯。於是,他開始剝開記憶中的傷痕,面對自己也去過、正對著香港高樓的那個高處,那裡很自由,卻也很致命。
這是非常深刻、動人卻也很沉痛的電影,拍攝孩子、青年「自殺」這種沉鬱主題,在商業市場畢竟不討喜。
但卓亦謙有他不得不拍的理由。坐在眼前的他,前刻臉上還帶著獲獎的喜悅,談起往事,表情瞬間沉了下來。
那是2009年一個常日,正在念大學的阿卓,看到朋友正窩在教室一角寫東西,「他很愛創意寫作,我還記得,他曾經只花了兩小時寫出一個溜冰場的故事,裡頭的小女孩、中年男子、還有其他人,在那裡展開了各自的新關係。」
他當時隱隱覺得朋友不對勁,但沒能做什麼,直到隔天他進了學校,才知道那個朋友竟然已墜樓身亡,自責、懊悔和很多很多的情緒瞬間衝了上來。
故友留了一封信給阿卓,6千多字,是用劇本形式寫出來的,他要阿卓為他保存10年,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10年。」卓亦謙鎖眉說,但從那時起,殘忍現實、被壓抑的年輕生命,以及自殺這個主題,已經成為他創作的重要主題。
而且,對阿卓來說,朋友的死和《年少日記》深沉的敘事,都不只是屬於角色和好友而已,「2016年,香港9月開學,前後好幾天,每天都有人跳樓……。」這是好幾世代的香港故事,甚至也是卓亦謙自己的故事,「朋友離開才讓我想寫故事,大學我寫東西也不是很厲害,但我覺得,我有點了解他的世界。」
《年少日記》不但是阿卓獻給朋友和那些墜樓青春的作品,更是阿卓對自己生命不斷反芻後的一本日記。
「憂鬱症。」卓亦謙很快提到了現代都會叢林裡的幽靈,「(病發時)腦袋想的事情會不合邏輯,至少不是常人的邏輯。那時候,人會不知道自己憂鬱,有太多心裡話沒辦法發洩,怪自己,又不敢跟別人說,覺得自己是怪胎。」
出身》香港官二代 自稱學業「失敗者」
卓亦謙沒有明說,但他或許跟電影裡的孩子有傑經歷過類似的童年。他父親卓永興和鄭中基飾演的大律師一樣,是香港傳統的精英,現在是香港政務司副司長。在電影中,那隻粉紅色河馬和另一個布偶,就像王家衛《花樣年華》裡的樹洞,主人們總抱著它們,傾訴內心深處的祕密。
「河馬是我爸爸1984年追我媽媽送的禮物,3年後,我出生,爸媽把河馬送給我,小時候,家裡沒人,我就會跟河馬玩,一直到現在30多歲,我還在跟河馬說話。」阿卓說。
電影裡的小朋友鄭有傑從小成績不好,「我學業也很差,回想起來,我高中可能就已經有憂鬱症了。」阿卓說,「我學業不好,我從七歲到高中,一直是個失敗者,公開考試(香港中學文憑考試)總分30分,我只拿到8分。那時我跟家裡關係也不是太好……。」
在《年少日記》中,一位弱聽高中生「蛋糕」,因為聽障被同學霸凌。卓亦謙猶豫了一下,終於說出了他自己幾乎相同的往事。「我其實也有弱聽,我聽人說話,有時要用猜的。」阿卓說,「高中就有人笑我,我很矮,如果要反擊,只能把別人推下樓梯。我很不開心,但學校沒有教我人與人的關係。」那時,阿卓要發洩情緒,只能裸著拳捶打牆壁。
「15歲時,我記得我看到電影《心靈捕手》,我不停地哭。」卓亦謙在電影中看到其他脆弱的靈魂,他也慢慢愛上了這種藝術。
即使學業不好,卓亦謙終於選好自己的路,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開始了電影的旅途。
長大很難,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大人也好難。大學時,卓亦謙歷經喪友之痛,畢業後難處同樣很多,他成了編劇,曾參與《今晚打喪屍》、《殺破狼.貪狼》劇本創作,但也就只有這兩個劇本順利被拍成電影。

低谷》曾窮到沒錢進帳 克制跳樓衝動
直到2019年,他決心拍下朋友的故事,正式藉著《年少日記》前身《遺書》獲選香港大專組「首部劇情電影計畫」繼續前進,但太多關卡要過,放棄的念頭幾乎沒停過。
生活無情地壓著他,最窮的時候,一個月根本沒有點滴進帳。「當時,我每天都在九龍灣小小的房間工作。」他秀出手機照片,那時候他整個人都腫,頭髮也掉了不少,每天睡在沙發床上,全身痛,只能靠止痛藥緩解,心裡的憂鬱更折磨著他,常常忍不住望向旁邊的大窗子,克制著跳下去的欲望。
他沉默了一會兒,此時,坐在他身旁的女友Genie忽然溫柔地勾住他的脖子,雙眼直勾勾盯著他。Genie也曾有情緒問題,兩人相戀後,Genie陪著他繼續修改劇本、拍攝,一直到剪輯,加上監製爾冬陞的督促,才終於完成這部作品。
「我希望這部電影,能讓留下的人互相擁抱。」得到金馬獎後,卓亦謙動情地說。一路走來,他一次次陷入低谷,但他現在遇到了Genie,終於發現自己有能力好好擁抱、好好傾訴,感動更多人。
「金馬獎這次開場影片中,張姊(張艾嘉)說:『電影會一直拍下去。』聽到後我就哭了,開場影片像是告訴我:『要繼續!』」卓亦謙說。
電影是記憶的一種形式,卓亦謙知道,無論記憶是否是缺憾,它們終究會成為珍貴的回憶。
戲裡,小鄭有傑總是彈不好德布西的《Reverie》,爸爸很生氣的錄了下來。在最後的最後,錄音機壞了,裡頭的東西卻沒人忘記。朋友的事、自己的事,痛苦的、美好的回憶,阿卓好好說完故事了。
時間更晚了,在餐廳外抽幾根菸後,卓亦謙真的累了,他脫下了他的緞面劍領西裝外套,就像古典畫作《馬拉之死》的構圖,垂手在矮椅上躺了下來。
不過感覺上,他並不孤單,身上散發著很強大的生命力,阿卓好好地把頭靠在Genie腿上,小河馬則在一旁笑著。
四周只有屋內隱隱傳來的人聲,但他們身後,像有人彈起了德布西鋼琴獨奏曲《Reverie》中的G大調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