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據WHO(世界衛生組織)統計,全球每8個人之中就有1個人患有精神相關疾病,台灣則至少有超過200萬個家庭正處於憂鬱風暴之中。
那一天,當前科技部長陳良基發現結褵40年的另一半站在16樓的陽台上打算縱身一跳時,他唯一的念頭,只有緊緊抓住她的手……
原本開朗大方的太太素梅嚴重失眠、變得沉默寡言、行動遲緩,害怕面對人群,宛如陷入憂鬱流沙,身體的自主能力一點一滴地流失了,而自信心、安全感也跟潰堤。當她越是心急、越是掙扎,就陷得越深;藥物副作用使得記憶漸漸空白,更令她感到失落。
「環境不是我們能控制的,但要不要笑是自己可以決定的。」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考驗,陳良基決心卸下部長職位,提前從台大退休。
除了安排太太接受精神科的專業醫療和心理諮商之外,他也每天按表操課地陪伴太太定期散步、做運動、追劇、出遊,鼓勵她寫下「煩惱筆記本」……經過兩年悉心照顧與一家人同心協力的努力,那個熟悉的太太又回來了。
罹患憂鬱症不是誰的錯,只是大腦生病了。身為守護者的你,若能用包容的心去理解,持之以恆的陪伴,就能看見痊癒的曙光。
陷入憂鬱的流沙
原以為過了60歲,人生走過了彎彎曲曲的小道、擁擠忙亂的車水馬龍大道,大喜或大悲都已經歷過了,不再會為任何事情所困。卻沒有想過,自己會陷入憂鬱流沙,當我愈掙扎、陷得愈深,彷彿進入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……
從外人的眼光來看,我的人生應該是快樂充實的。朋友說我簡直就是人生勝利組,家境小康,成績總是名列前茅,高中就讀第一志願北一女,大學則是成功大學電機系。
成功大學電機研究所畢業後,我的就職之路順利;結婚後,先生爭氣,孩子也很優秀。在經濟上沒有什麼後顧之憂的我,選擇了提早離開職場,在博物館擔任志工,並且參加社大課程、合唱團體,日子過得看似無憂無慮,但是,62歲那一年,我卻陷入憂鬱的泥淖,無法自拔。
2019年11月15日,初秋的台北街頭已有寒意,良基打電話回家,告訴我他要下班了。我嘴上沒說什麼,心底卻有點驚慌,下意識地搬了一張椅子,到陽台上站著。
我趴在16樓的欄杆邊,往下一看,正下方是紅綠燈等候區,黃昏時刻的信義路上人潮熙來攘往,人真多啊!我怔怔看著,裡面有剛結束一天工作想趕回家的上班族、有揹著書包可愛的學童,遠方的燈火陸續亮起,但我的心卻很灰黯。
事實上,我的內心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感到沉重、灰黯,生活中感覺不到一絲愉悅,彷彿走在黑洞裡,永遠看不到出口。難道我的餘生就要如此痛苦地度過?這樣實在太恐怖了,我一心只想要解脫。
我遠遠望著樓下的人群,忽然想到好多年前,有個肉粽攤販被跳樓自殺者壓死的新聞,鬧得沸沸揚揚。我想,如果我要跳樓,絕對不能傷害到任何人。我的心中有了打算,那就是大樓人行道必須清空,不如請一樓的警衛幫忙吧!
我走回客廳,打了通電話給一樓警衛:「你好,請幫我排空人行道,3分鐘後,我要從陽台下去。」
我告訴自己,再過3分鐘,我就可以解脫了。
3分鐘後,我站到陽台,爬上椅子,翻過圍欄外緣,兩手順著欄杆往下滑,卻沒看到警衛出來清空人行道,路上人潮依舊。
「我等了那麼久,怎麼人還這麼多呢?」可能警衛把我的話當作是開玩笑的惡作劇,因此沒有理會我。
16樓的風好強,我緊緊抓著欄杆,手不敢放,但是我也沒辦法把自己拉上去了。過不了多久,等我力氣用盡,只能摔下去了。
.jpg)
在這之前,我去精神科看診、用藥已經持續兩個月了,心情完全沒有好轉。雖然安眠藥讓我可以不失眠,但只要醒著時,就像是失了魂的女鬼,整顆心都漂浮著、懸在空中,不知道安放在哪裡。
良基在家時,為了不讓他察覺出異常,我還會硬撐著裝作沒事,維持生活日常;但是,等他出門去科技部上班時,我連假裝都不需要。
一整天下來,我癱在沙發上,看著陽光灑進屋裡,光影緩慢地移動。我知道自己應該要站起來活動一下,但是身體卻動不了。
我不想做任何事,不想跟任何人說話,書讀不下,影集也無法吸引我的注意力,聽到以前喜愛的音樂旋律,甚至會害怕。
那種無助的感覺像是眼前有片深藍色、令人窒息的流沙,逐漸淹沒了我的身體,想要將我吞噬;我愈掙扎、愈下陷,空氣也愈來愈稀薄。
怎麼辦?我已經失去了生活的能力,再也沒有快樂的能力。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?如果能夠解脫,拜託,請讓我解脫。
我的腦海裡翻來覆去,盡是各種解脫的辦法。我不能傷害任何人,不能有機會被救起。
※今周刊提醒您,自殺解決不了問題,請給自己一個機會 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:0800-788995;生命線協談專線:1995
兩週前,有位良基熟識的企業名人,因為憂鬱症跳樓了,我看到新聞報導時,忽然決定,那就選擇跳樓吧。
這一兩個星期,我前前後後在陽台探勘了好多次,該從哪裡跳下去比較好呢?從後陽台往下看,是層層疊疊的遮雨棚浪板,有這些浪板阻擋,跳下去可能會受重傷。如果身體殘缺了,就會連累到家人,他們必須終生照顧我,這對我來說,比死還要痛苦。
我曾經試了好幾次,把椅子搬到前陽台,打算撥電話給警衛請他幫忙清空人行道,但警衛一接起電話,我就急忙掛掉。原來,這麼極端的行動,我還是會猶豫,會害怕。
但這次,我不能再拖下去了,良基再過十分鐘就要到家了,如果今天不跳下去,又要行屍走肉地度過一天,什麼事情也不想做,什麼事情也做不了,我已經成為了一個廢人。
要是我現在走了,良基還可以找得到另一個可以陪伴他下半輩子的伴侶,而不是像我這樣的負擔。
我爬出陽台圍欄,跨過欄杆上緣,雙手握住欄杆下滑,一點也不害怕16樓的高度,只是要等候時機放手。沒料到我的腳居然碰觸到堅固物,本能地踩在15樓的欄杆上緣,還可以支撐一下。可是底下的行人還這麼多,我不想要傷害到任何人,但抓住欄杆的手遲早會力竭,這個時刻來臨時,我就自然解脫了。
就在這時候,聽到良基進門的聲音了,聽到他如往常一樣呼喚著我的名字,感受到他找不到我的慌張。突然之間,感覺到有雙手緊緊抓住我還拉著欄杆的手,是良基,他不斷喊著:「不能放手,抓緊我!妳忘了嗎?結婚時我們發誓過要照顧彼此到老的!妳怎麼可以拋下我?抓好我的手,不能放!絕對不能放手……」
沒多久,消防車到了,兩位消防人員破壞了門鎖衝進來,另外幾位隊員則從15樓陽台抓住我,替我繫好安全繩索,晃晃悠悠地,我被帶進15樓,這戶人家看到這一幕,大概也嚇到了。
接下來的事,很多我都不記得了,只記得一些零碎片段,就像是散落在相簿裡的褪色相片:這一張,是我被送去醫院急診,被診斷為「重度憂鬱症」,緊急安置住院。這一張,是我醒來看見良基在病床旁邊辦公;這一張,是原本在波士頓工作的大兒子學中趕回來,在病床旁邊呼喚著我;這一張,學平下班後來到病房,整晚和哥哥一起陪伴我。
我好累好累,外界的一切都像隔了一層膜,醫院裡蒼白潔淨的氣味,讓我只想睡。我不知道醫師跟家人說了什麼,總之,他們決定讓我做ECT(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,電痙攣療法),那是一種以電療消除近期記憶的治療方式,就像 MIB 電影中記憶清除筆的作用。只是,ECT 至少要做6次,超過12次效果比較好,因此我每兩天就得接受這個治療一次。
.jpg)
為什麼是我?—當憂鬱症來敲門
當憂鬱症來敲門,人們第一個會想到的往往是:「為什麼是我?」
身為一個過來人,我想說的是,得到憂鬱症絕對不是你的錯,就像人會得流行性感冒、腸胃發炎、甚至罹患惡性腫瘤,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悄悄發生的。問這個問題,只是為了找出心底的結並將它打開,幫助你更理解自己而已。
精神科醫師告訴我,造成憂鬱症的原因不只一種,當生理因素、人格特質和壓力等因子重疊在一起的時候,就容易讓人承受不住而發病。
第一個,是生理因素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曾經追蹤三代家庭超過20年,發現父母及祖父母都有憂鬱症的孩童中,有超過一半的孩童在成為青少年之前就被診斷出精神失調;也有很多研究資料顯示,罹患憂鬱症的父母,其小孩罹患憂鬱症的機率可能性較高,但並不代表憂鬱症一定會遺傳。
其次,是人格特質。像是容易壓抑情緒、做事認真拚命、責任感強烈、屬於完美主義者,也比較容易罹患憂鬱症。
「我的憂鬱症患者,很多都是大好人,」醫師告訴我:「他們往往個性溫和體貼、什麼事情都先替別人著想,甚至可以說是有點濫好人。」
另外,當有重大事件發生或生活型態產生變化,也容易引發憂鬱症。譬如升遷、失業、失戀、結婚、生育、事業失敗、新居落成、家庭衝突……發生在人生不同階段的事件,這些改變都有可能造成心理壓力,導致憂鬱。
我覺得,生活就像在爐子上燒開水,每個人都是一個水壺,能力愈強、心愈大,裝的水就愈多,而生活壓力就像底下點燃的火。如果水煮沸了、火未熄,大水壺從壺口「噗」地噴洩出來的水,就會氾濫成災。
有時我會想,如果我只是一個小水壺,是不是就不會發生這一切了?小水壺很容易裝滿,不時得倒一些出來,宣洩一下內在壓力,身心或許會比較健康。但那時候的我不明白這個道理,覺得自己只要夠努力,什麼事都可以辦得到。
我分析憂鬱症找上我的原因,或許從小生成的「Yes Girl」個性是關鍵之一;另一個原因,是生活中突如其來的壓力。
我很痛苦,但是我不孤獨
良基為了我的病,毅然決定離開部長職位,並決定提前自台大退休。我明白他是個事業心很重的人,卻當機立斷、放下一切來照顧我,讓我非常感激。
但那時我也會自責,自己是否終究還是成了煩惱筆記本上寫的:「現在的我,已經成為良基人生中的負擔。」
「如果,我永遠……不會好,怎麼辦?」我拼湊了很久,才能完整說出這一句話。他毫不以為意,先是安慰我:「不會永遠這樣的。」接著他想了想,又說:「就算不會好也沒關係,我會永遠陪著妳。」
那時,原本感覺自己像個沙漏,自信、能力、安全感……都不斷從我身上流逝,但神奇的是,他這句話就像是強而有力的一隻手,止住了我不斷流失的安全感,平息我內心的焦慮。
是啊,我很痛苦,但是我不孤獨。我還有始終守護著我的丈夫、惦記著我的親人和朋友,以及就算我不吭聲也在電腦那端嘰嘰呱呱說個不停的小孫女。
當憂鬱症來敲門,或許我真有不幸;但是只要願意抬起頭看看天空就會發現,我是活著的,我是幸福的。
不要急,慢慢來,他們都願意給我時間,陪伴著我,等著我康復。
.jpg)
學習整理人生行囊
疫情期間,我跟良基每天都會去住家後山的步道散步。從前總是把周圍人的需求放在前面,漸漸地,除了敘述劇情之外,我也會跟他說起陳年往事,說起生活中許許多多的困擾,或是婚姻關係裡,在哪些事上我覺得自己受了委屈。
良基總是靜靜地聽著,有時他會答腔,有時辯解,我又再反駁他……看他一臉笑咪咪的樣子,原來是在引誘我多說一點話呢。
「妳心裡壓抑了大大小小的委屈,卻連自己有這種感覺都很自責。」良基說:「這不是妳的錯,覺得委屈才是正常人。妳要講或不講都可以,但是妳不需要再繼續背負這些事。」
他從前沒有講過這樣的話,讓我很感動。靠著心理諮商師跟身邊家人的鼓勵,終於,我漸漸清除了心底的垃圾。
如果說人生是一場長途跋涉的旅程,我們都是背著沉重行囊的旅人,走過的歲月都是行囊的重量,本以為行囊裡面的東西都是必須的,從來沒想過要整理它,但其實肩上揹著的往往是過重的行李。
日常生活裡我是個收納高手,可能也因為這樣,把好多情緒都「收納」得太好,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清理,也沒打算請別人幫忙。
我曾以為給別人看到行李有點害羞,殊不知它太重了,讓腳步愈走愈踉蹌,以致跌倒了。
這時候應該找個地方把行囊放下來,自己清理也好,向外求助也好,把不需要的東西扔掉,需要的東西,擦拭乾淨再放進去。
人生的道路這麼長,一面走、一面梳理,才不會耗費過多的力氣過日子,才能走得更遠、更穩。
※今周刊提醒您,自殺解決不了問題,請給自己一個機會 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:0800-788995;生命線協談專線:1995
作者簡介
王素梅
成大電機碩士。
在大家族中成長,養成了隱忍求全、堅毅不拔的個性。希望藉由分享自己掙脫憂鬱流沙的經驗,幫助所有受憂鬱症所苦的患者與家人。
陳良基
曾任科技部長、台大副校長,現為台大電機系名譽教授,是國際知名IC設計專家,也是台灣創新創業教育及AI的重要推手。他以守護者的身分,陪伴另一半走過憂鬱幽谷。著有《創新的人生》。
採訪 鄭郁萌
成大中文畢、輔大傳播碩士。
曾獲洪醒夫小說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卓越新聞獎、台灣醫療新聞獎等。目前任職媒體。
本文摘自時報出版《牽手就不放手 :我們一起穿越憂鬱流沙》









.jpg_280x210.jpg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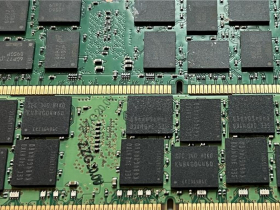
_20250624163455.jpg_280x210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