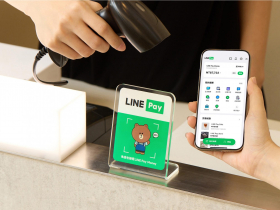通姦除罪化是為了避免再有性侵受害者默默吞下,然而社會價值觀的毒瘤卻還沒拔除。今周刊特別採訪勵馨基金會的執行長紀惠容女士,以及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馮喬蘭女士,探討社會的刻板印象如何奪走性侵受害者的話語權。
「裙子穿得這麼短!」、「為什麼要喝得爛醉?」、「這麼晚了還待在酒吧!」這些耳熟能詳的質問,常常是性侵受害者在案發後常常需要面對的責難。讓受害者感到痛苦的,除了精神與身體上的傷口,還有無以名狀的「恥感」。然而這種恥感的形成原因,在於我們的社會總是慣於嚴格檢視被害人的言行、衣著有無符合「端莊」的形象。
文化當中,責怪被害者,是全世界的通病。但我們是否想過,這些不帶同理心的質問下,受害者要如何開口求助?當他們無法開口求助,社會就失去向他們伸出援手的機會。
紀惠容女士表示,性侵害的犯罪黑數是通報案件的(註)十倍,也就是說選擇報案或被揭發的案例,只有實際發生案件的十分之一。而剩下的十分之九為什麼選擇不求助?因為受害者對於選擇報案後,將面對的社會反映沒有安全感。
「許多人對於自己沒有經歷過的創傷缺法想像,所以社會常對受害者不夠友善。」紀惠容女士在受訪時曾如此說道。
社會大眾一句「為什麼是你,不是別人?」就把受害者打到谷底,更何況在暴露自己受害的經歷後,要面對「有奮力抵抗嗎?」、「為什麼不選擇逃跑?」諸如此類的問題。不僅逼迫受害者自省,也是對他們的二度傷害。
面對社會的放大檢視與對受害者不夠有善的司法程序,被害人常常要反覆被質問,甚至被認為會受害,自己也有責任。每一次的求助與每一次的開庭,都在不斷被質疑的情況下,開始責怪自己為什麼不逃跑、為什麼不拒絕。
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,案發當下,受害者可能別無選擇。
曾經有國小老師利用師長的權威,以寫聯絡簿向家長告狀為威脅手段,在害怕被家長責罵的情況下,學生不得已只得忍受師長的長期性侵。再者,也曾有女孩在遭遇侵犯後,從一開始的奮力掙扎,到最後選擇放棄抵抗被性侵得逞。原因是害怕自己當時單獨面對加害者的情況下,逃跑或抵抗會有生命危險。
除了上述的兩個例子,社會上有數不清的案例,案發當下受害者的反應與應變措施都有其不同的理由。這麼多我們無法想像的情況,我們卻用同一套標準去衡量應變方式,再以案發的事實來質問被害人,而不是來譴責加害人的罪刑,這對受害者而言著實欠缺公平。
其實台灣對於性教育的認知都僅有中、小學課本中對生理構造的介紹。對性的自主權、社會看待性侵案件的角度,我們的社會都還沒有建立一套確切的思想價值。
教育,是改變偏見、建立正確價值觀的第一步,也是能夠影響整個社會更尊重每個個體的核心方法。
透過教育和同理心,我們才能成為一個「對他人遭遇的處境更有想像力的人」,當我們對於他人的痛處與害怕更能感同身受,了解受害者的困境、友善的幫助就再也不會只是個口號。
屏除制度面,我們能為性侵受害者做到的就是慢慢的改變每個人的價值觀,剔除社會對受害者的偏見之外,也希望讓他們了解:所有不幸發生的事,錯不再受害者。
思想的改變是個浩大的工程,但需要整個社會中每個人的參與。就如同馮喬蘭女士在採訪的最後所言:「當我們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想成為幫得上忙的人,那麼,這個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才能夠扎實。」
註:犯罪黑數是指已發生的刑事案件中,沒有被列入官方正式統計的犯罪數量。










_20250828181818.jpg_280x210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