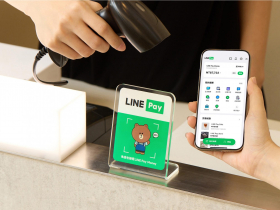(今周刊1436)
受邀於今年「台灣大未來國際高峰會」發表演說,國際知名經濟評論家馬丁‧沃夫坦言,關於下半年,自己可以列出一籮筐的風險,但若論最擔心的事,他把矛頭對準了地緣政治,以及被他稱為「鬼牌」的川普。
「情況或許會令人滿意,但仍難以預測。」接受《今周刊》專訪時,馬丁.沃夫(Martin Wolf)以這句話總結他對二○二四下半年的看法。
作為《金融時報》(Financial Times)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家,馬丁.沃夫的評論以分析扎實、筆鋒犀利及批判大膽聞名。他的朋友圈遍及全球重要財經官員、經濟學家,許多重大經濟政策的制定,主事者也會特別與他溝通,希望得到支持,就像2009年,美國財政部推出為金融機構清除不良資產的「排毒計畫」(PPIP),當時的美國財長就特別致電馬丁.沃夫要求支持;不過,他隔天寫在《金融時報》上的專欄,仍是一頓直言批判。
「該怎麼說、就怎麼說」的馬丁.沃夫,如今對於今年下半年的全球經濟展望,卻給了這樣一句讓人略感模糊的評論。他究竟是怎麼想的?
「或許令人滿意……,是因為大環境應該會持續朝著『正常化』前進。」他表示,經濟正在復甦,美國通膨雖稍有黏滯,不過已經比許多人擔心的更快降溫,因此,「貨幣環境也會漸漸正常化。」他預期,利率固然不見得會回到2021年以前的水準,但對比於目前美國聯準會(Fed)目標利率高達5.25%至5.5%水準,接下來,「名目利率約4%到5%、通膨維持在2%」可能會是新常態。
至於所謂的「不可預測」,「我現在就能列出一大堆下半年可能發生的風險……。」馬丁.沃夫隨口舉例,在全球債務升高,利率也處在高檔的環境下,「我有絕對的理由,擔心另一場金融風暴可能發生。」循著這個擔心,他開始談到了聯準會主席鮑爾(Jerome Powell)的利率決策。
擔憂一〉降息不是單行道 過度謹慎反而耽誤時機
今年6月,歐洲央行宣布降息1碼,這是自2019年9月以來的首度降息,相對於鮑爾的降息態度仍然曖昧,《華爾街日報》在歐洲降息後立即評論:「歐洲央行與美國聯準會,可能開始走向不同的路。」
但是,哪一條路才是對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