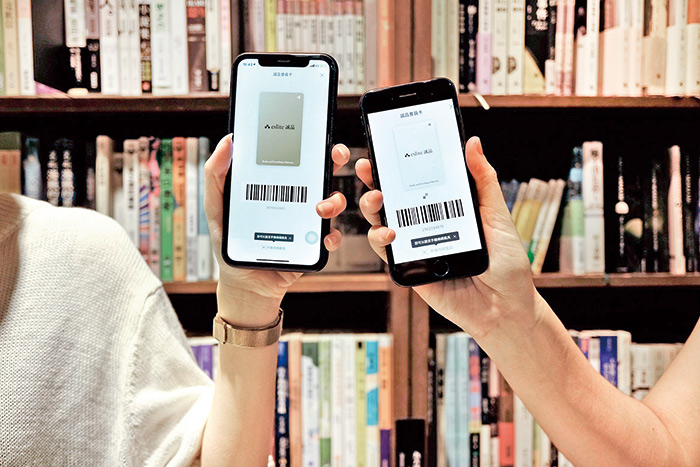今年上半年,吳旻潔展現果斷的據點整頓決心,一口氣關閉6家店;下半年預計再關4家,包含中壢SOGO店、營業坪數最小的捷運書店與東湖店,以及中國深圳店。台灣9家店加總營業面積占總營業坪數約3%,對實質營收衝擊則小於3%。但是,許多人對於誠品一連串的關店策略,仍難免產生疑慮與憂心。
「能在今年果斷地關店,是因為我們的全通路發展已經準備3年多。」吳旻潔用富有特色的娃娃音,不急不徐地回應這些天外飛來的憂心,並且開始闡述她醞釀3年、斥資5億元的數位轉型,要讓誠品連結起線下線上的全通路概念。

吳旻潔做出籃球防守姿勢,生動呈現夢境場景。(攝影/吳東岳)
談數位轉骨 結合線上線下 打造全通路
2004年,吳旻潔剛踏入誠品不久,誠品高階主管曾大力建議吳清友建置數位平台,為此,吳旻潔做了一份報告,網羅誠品上下員工、外部企業家的意見,提出誠品是否有發展數位的必要性。
吳旻潔甚至還跑去請教網家董事長詹宏志,「他聽到誠品想做電子商務(EC),就用做一本刊物與雜誌是不同的比喻來解釋;提醒後者的營運模式涵蓋定價策略、文章主題等,要考慮的變數不同於只做一本刊物……。」
吳旻潔認為,詹宏志在提醒,誠品應思考當時是否具備做電子商務的基因。接著吳旻潔大笑著說:「當時的吳先生可能更想多開一間實體店。」誠品發展電商的想法也就此暫時擱置。
隨著電商發展的不斷演進,吳旻潔也不斷將誠品放在電商的場域中思考。「當然會希望誠品永續,但首先要想,下一個5至10年,它應該要怎麼樣轉變?」吳旻潔顯然認為,照舊模式,誠品是無法應付網路所帶來的商業變化。
然而,誠品的特殊定位,放眼望去,其實找不到太多範例能參考。「譬如說全聯、momo,他們較偏向民生物資,而非內容。」吳旻潔觀察,誠品則不同。
「如果沒有實體空間的話,感覺誠品就像一門生意,沒有特別,也無法體會到空間跟美,更不能在裡面想像、做很多事情。」既想要保有誠品在實體世界所擁有的獨特品牌力,又想跟上網路帶來的改變,吳旻潔一路以來思考的,都是如何不屈從於電商拚價格、重口味的行銷模式,走出誠品自己的數位轉型。
她的體認是「創一個電商平台也許很快,但要真正打通各社群媒介、平台等,並串聯線上下,至少要花2、3年。」
談內部革命 組新團隊 要同仁駕馭工具
今年9月,誠品先端出大菜——誠品人App與新會員制。年底「誠品線上」緊接著登場。這是吳旻潔一路匐匍前進,不斷嘗試錯誤後的成果,背後整編了包括10年來從未更變過的POS系統、以為買套裝軟體套用就可以的網路書店後台,到CRM(顧客關係管理系統)全新上線,每個調整改變,都經歷「至少失敗一次」的痛苦歷程。
回頭看,2000年上線至今的誠品網路書店,僅占整體營收2%,因為「以往誠品是以店鋪為核心。」要做數位轉型,就要用新腦袋,帶入新思惟。於是,她從外部找到專業主管,打造一支約40人團隊,名為商業運用與技術創新小組,展開一連串打掉重練的內部革命。
吳旻潔第一步先整理誠品臉書、Instagram等社群平台;緊接著第二步導入CRM系統,快速累積消費者軌跡,並轉化為有價值的資料。「就能夠針對特定族群辦活動或推播訊息;樓面改裝、擺設等也都能參考。」吳旻潔說。
踏出的第三步,便是推出新會員制度與誠品人App,以提升黏著度,新推出的App上線首日即獲iOS系統不分類及生活風格類免費排行的第1名。目前誠品會員約有257萬人,其中25歲至50歲約占7成,這群消費客群對數位相對不陌生。「誠品自此要抓住客人當下的需求。」吳旻潔下了這樣的註解。
數位思惟帶動的內部革命也因此隨之展開。她解釋,誠品同仁們正學習如何駕馭這些工具、改變思惟,因許多思惟與制度需要重新建置或破除,一旦換腦袋成功,「線上訂貨、線下取貨,顧客在誠品將是無縫接軌狀態;並提供個人化服務,打造一致性顧客體驗。」
為了支撐起誠品的虛實整合,誠品自2017年就開始找地,準備倉儲物流空間。「剛好誠品總經理(李介修)是這方面專業,能在台商回流前找到地,真的很幸運。」年底將啟用的物流中心,成為誠品數位轉型的大後盾。
最後1里路,則是年底將上線的誠品線上平台,吳旻潔認為,此時的誠品,將從以實體店鋪為思考的經營,轉換成以人為中心、以會員為核心思考的全方位服務。
讀冊生活董事長張天立注意到誠品的轉型,他提到發展數位與傳統經營空間截然不同,且虛實整合是一大困難。「建置需求、所需人才都不一樣,加上投資電商與數位有如無底洞。」不僅如此,他指出,實體店面如何持續營造人文薈萃氛圍,形塑集客力與人文魅力都是誠品的考驗。

疫情下,誠品在香港逆勢展了兩間店,吳旻潔欣喜地秀出排隊人潮照片。(圖/誠品提供)
談社區小店夢想 融入當地居民的日常
數位轉型到位,讓吳旻潔今年一口氣關掉10家店,並不表示實體店將萎縮,相反地,誠品將在台灣各地抽長出「社區小店」的綠芽,這是一直種在吳旻潔心中的夢想。
「誠品20周年,林懷民老師曾許願319鄉都有誠品。」吳旻潔十分認真看待這件事。「但誠品虧損15年的主因是開錯店,許多小店都是叫好不叫座。」因此評估進入都市外的區域的可行性,必須格外審慎。
回顧過去,吳清友自2004年將誠品從書店轉而發展文創產業,第一步就是擴大店裡的選品量,隨著敦南店型獲利,默默確認「關小店開大店」的經營策略。
「2016、2017年看到家樂福開始發展小店,我就跑去跟吳先生說希望研發小店。」當時吳旻潔還用自己的生日命名專案,以宣示決心。沒想到吳清友驟逝,她暫緩計畫,將重心放在2018年將開的誠品南西店與中國深圳店,「小型店就這樣一直擱著……。」
但隨著網站、App就緒,吳旻潔埋在心裡的夢想再度點燃。建築大師姚仁喜曾說:「去誠品有一種歸屬感,好像去了一個安心的地方,一個屬於你的地方。」在吳旻潔想像裡,社區小店將不超過150坪,要融入當地居民的日常,成為他們心中能安頓的空間。
「希望靠社區居民與活動去創造特色,實現誠品的場所精神。」她透露:「先嘗試一家,並邀請對誠品『愛之深,責之切』的人去挑剔一輪後,再模組化。」至於店鋪設置地點,誠品內部幾經激烈辯論,「舉例來說,我認為要幾個縣市各撒一家看看;但有另外一派則覺得要從台北開始,先將之前關掉的店鋪補足。」
即使發展小店,誠品在都會中心的大型店鋪,仍會維持一定能量與指標性。今年投入改造的誠品信義店、松菸店、台北車站地下街和新竹巨城店為例,信義店自6月取代敦南店24小時營業後,2個月以來書區業績成長1千萬元;新竹巨城店改裝後,7月業績也較去年同期成長5成;海外布局也未停止,今年香港新開的2家店面更出現排隊人潮,消費者很快回到實體店逛店、買書,享受誠品獨有的氛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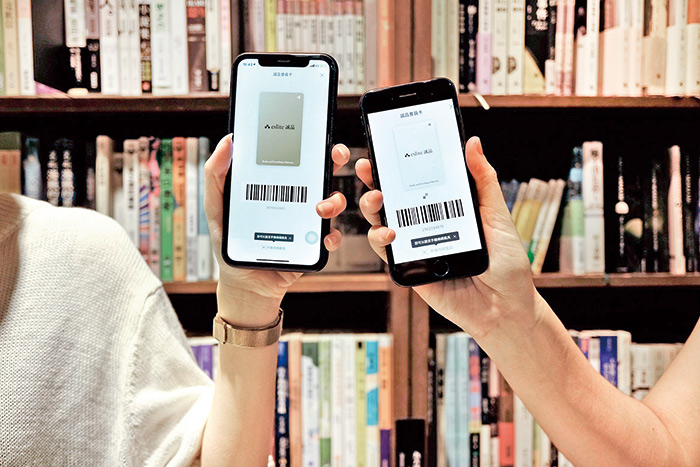
誠品九月推出全新誠品人App,以及會員制度,新增「黑卡」與「小童學卡」。(圖/誠品提供)
談黑暗中的挑戰 唐鳳啟發 不對未來做假設
對吳旻潔而言,夢境中青蛇的威脅,至此應是如釋重負,她已摸索出篤定的方向。
今年4月,她曾與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對談。「今年遇到最精采的對話,就是跟她。」唐鳳口中的誠品是「能成為線上下共同創作的空間」。等於替誠品未來的全通路平台做出新的詮釋,意外地,與吳清友曾說過的「誠品是台灣社會的集體創作」遙相呼應。
吳旻潔回想,她問唐鳳這輩子還有哪些想完成的事情,唐鳳的回答是:「這輩子我已經過完了,對我來講,這輩子就是過到上一刻。」
「當下我有被電到的感覺。」吳旻潔聯想到佛法講的「活在當下」,不對未來做過多的假設與計畫,正如數位就是不斷變化、時刻嶄新一般。
「很多人對誠品的標準與期許是非常高的,其他地方能容忍的,在誠品卻不行……。」吳旻潔似獨白地說著,接棒3年多,遇上風雨如晦,她並不驚惶,下半年起,誠品營運若能逐漸回歸,意味著,最壞的時刻應該過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