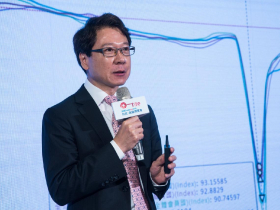醫生固然有治療病人成功的喜悅,也常常要面對病人很可能死亡的無奈。醫生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厲害......當勝利投手容易,當敗戰投手很痛苦。你願意承擔嗎?
我念台大醫學系五年級時, 進醫院當見習醫生。穿上白袍的第一天,難掩興奮,滿懷信心走進急診室,沒想到遇上的第一個病例,就讓我終生難忘。
那是一對新婚夫婦,兩人剛度完蜜月回來, 結果新郎卻碰上工安意外,鷹架倒塌砸到他的頭,送進台大醫院的時候已經腦死了。由於加護病房的床位有限,像這類被判定腦死、治療也不會有效的病人,就被推到急診室的一角。
我這個才初出茅廬的小小見習醫生, 只能無奈的看著患者嘴裡插著管躺在病床上,新婚妻子則淚眼汪汪坐在旁邊......忽然間我發現,當醫生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快樂的事,我們不見得有辦法把每個病人都救回來。
這是我當醫生第一天就學到的教訓。
從醫療的科技叢林回歸謙卑與人性
我的前半段人生很順利, 三十五歲就當上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。雖然考醫生是爸爸替我填的志願,但我一直非常認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
每天早上七點就出門,騎著腳踏車到醫院上班,夜晚十二點才回家,從醫的三十年間,我就在中山南路的兩邊來回,除非出國參加醫學會議,否則不論過年過節或颱風地震,我天天都上工,即使回家手機也是二十四小時開著,讓醫院同事隨時找得到我。
年輕時滿懷懸壺濟世的熱情, 曾經有過「地獄不空, 誓不成佛」的衝勁,後來我發現,地獄實在太大,裡頭的人根本救不完。而且開刀救人分秒必爭,很多時候我必須在三十秒之內決定病人的生死,於是慢慢的,情感成了奢侈品,我的眼中只剩下病歷。
後來醫生當久了, 不免覺得自己很厲害。因為現代醫學技術進步,心臟不好有機械性循環輔助器; 肺臟不好, 有呼吸器; 肝臟不好,有新鮮冷凍血漿可以做血漿交換;腎臟不好,看是要做腹膜透析還是要血液透析;腸胃道不好就打點滴,人根本可以不用吃飯;骨髓不好的就輸血, 不管輸血小板、紅血球還是白血球都可以;。
身體有感染可以打抗生素, 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的抗生素, 一路打上去......好像不管哪一個器官壞掉,醫學都有辦法應付。那時候我覺得自己簡直就像是王國維講詩的境界:「昨夜西風凋碧樹,獨上高樓,望盡天涯路。」
甚且, 葉克膜技術的成熟、心臟移植的發展, 讓很多原本束手無策的疾病,例如猛爆性心肌炎,都變成我的成就之所在。一連串成功的案例,包括邵曉鈴、星星王子等等,讓病人起死回生,更讓我以為原來「人定勝天」就是如此。
然而, 四十歲以後,我整個人卻慢慢感到頹廢。因為時常有很多病人,我覺得他應該可以活、應該能過關,卻在治療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撐不下去。
曾經有個病人因急性心臟衰竭而裝上葉克膜, 經過治療後, 心臟功能逐漸恢復,後來做了超音波檢查確認,預計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葉克膜拆掉,從加護病房轉往普通病房。
結果當天夜裡,住院醫師打電話來對我說:「柯P,你快來醫院!」 我問為什麼? 他說:「不要問,你來就對了。」我趕到醫院一看,嚇了一大跳。那個預計隔天就要拔除葉克膜,病情穩定可以轉出去的病人,或許因為睡覺時煩躁不安,在病床上翻來覆去,結果把插在股動脈上的管子掙脫了。
這下不得了, 葉克膜一分鐘的血液流量是2000CC, 大量的鮮血從脫落的管子往外噴,整間病房好像發生凶殺慘案一樣,大出血造成嚴重的休克,很遺憾的無法搶救回來。我當時心想,要怎麼跟病患家屬解釋,前一刻人還好好的,下一刻卻不行了?
當然, 有的時候也會發生, 我認為「這個病患應該沒辦法過關了」,但最後不曉得為什麼他能撐了下來。
一次又一次的衝擊,加上常有治療失敗的挫折, 慢慢的, 我領悟到,醫師是人、不是神,醫學是有其極限的。慢慢的,我重拾謙卑之心。慢慢的,我又從「科技」回到了「人性」。
救與不救都是醫師的煎熬
醫生固然有治療病人成功的喜悅, 也常常要面對病人很可能死亡的無奈。醫生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厲害。即使身經百戰如我,也常常會遇到無法處理的難題。
身為急重症醫師, 我經常會陷入兩難抉擇: 要救病人活命就必須截肢,但這樣的生命是否還有意義,到底要不要繼續掙扎搶救?尤其是面對焦急的家屬詢問病情變化為何出乎意料, 我又很難向家屬說明,其實很多時候病情變化根本不是醫師所能掌控。
我常半開玩笑說: 我們和ICU( 重症加護病房) 的病人無怨無仇, 卻很無奈的讓他們「不得好死」。
醫療科技的進步超乎想像, 延續生命不是問題,但醫生要面對越來越多倫理的問題:是否要用盡一切醫療手段,讓病患苟延殘喘的活著?或者何時要收手喊停?所以後來我常用一句話提醒醫學系的學生們:「醫生不是每個c a s e 都救得回來!當勝利投手容易,當敗戰投手很痛苦。你願意承擔嗎?」
(本文摘自《生死之間︰柯文哲從醫療現場到政治戰場的修練》,商周出版,柯文哲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