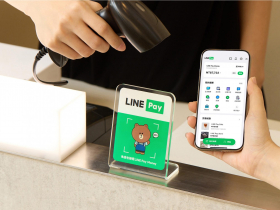二○○○年的夏天,我帶著即將完成國家衛生院婦癌專科醫師訓練的六個學員,到美國參加美國婦癌學會,順道拜訪美國西岸幾個主要的癌症中心。參訪結束前,訓練計畫的國際老師──知名婦癌專家里奧.拉加西(Leo Lagasse)教授在他洛杉磯的家裡設宴款待我們。
當時已年近七十的拉加西教授在臨床上仍然非常活躍,並且積極從事援助第三世界的人道醫療計畫,十分受人敬重。
同為婦癌醫師,很自然地,我和他聊起了面對癌症不斷帶走我們的病人時,無數令我無能為力的心碎時刻。
被卵巢癌纏身的她:有一種無奈叫心痛
我舉了一個赴美前不久照顧的一名病人吳小姐為例。吳小姐是卵巢癌病人,最早在其他醫院開刀,但主刀醫師打開肚子、割傷腸子後,再把肚子關起來說:「這沒辦法再開刀了!」吳小姐才被轉送到馬偕醫院來。
我們組成外科照顧腸子、泌尿科照顧膀胱,再加上我所帶領的婦產科醫師,讓曾被其他醫師認定「不能開刀」而放棄的吳小姐,經過一連串的手術及治療,能夠存活下來,並且度過了很長一段生活品質極佳的時光。
這樣持續了五年。五年之中,她不但恢復工作,生活平順,並常藉著門診返診時和其他病人互動,鼓勵心理脆弱的新病人。我們在這段期間建立了很深的醫病友誼。
然而,不幸的消息傳來。一天,吳小姐返診時告訴我,她持續咳嗽好幾週,我立即安排她做胸部X光檢查,發現肋膜積水及肺部轉移病灶,確認是卵巢癌復發,並轉移到了肺部。
吳小姐問我:「還有多少機會?」由於一旦卵巢癌復發,且已出現遠端轉移,就幾乎沒有治癒的機會,我只有據實以告,並說明此時的治療目標會在控制病情、延長生命,並改善生活品質。
但她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──這一回,不是醫師放棄了她,而是她放棄了醫師,轉而投向聲稱可以「包醫」的非正統醫療。期間,我與我太太都努力地勸她要回來繼續進行正規治療,仍無法改變她的決定。
不久後,吳小姐還是進到了醫院急診,呼吸急促、形銷骨立,轉到病房來後,我能做的事更有限了,只剩下最後的支持療法。
一天,我在看門診的時候,病房的護士小姐告訴我,吳小姐說她想回家了,我立即趕往病房探視她。推著吳小姐的推車在病房走廊邊,正要離去。見著我來,她勉強擠出了淡淡笑容,以最後的力氣、微弱的喘息聲,在我耳邊說出:「我希望最後,在家裡。」然後對我說出感謝和道別。
面對婦癌,老教授也只能淚眼以對
在與拉加西教授談話的當下,我仍能感受到那種心痛。我問這位久經沙場的老教授:「當我們自己一再重複這樣的心碎時刻,我們無以自處、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面對這樣的哀傷,當你長期照顧的病人已經變成你很重要的朋友時,你最後要送走他,這時候,我們要怎麼處理這樣的感情?」
我止不住激動再接著說:「你要怎麼教導在座其他的年輕醫師,要投注感情於這樣的工作,可是卻要堅強地面對?」
我並沒有得到老教授言語上的回答。但那一刻,我清楚地看到他眼眶瞬間泛紅,眼角有晶瑩的淚珠閃爍,我已明確知道,我們有相同的經驗與哀傷,也明白,這是婦癌醫師無法避免的難題,即使有再顯赫的資歷、再豐富的經驗,都可能不會變得熟練或無感──如果我們對病人投注了感情,眼淚,是唯一的答案。
哀傷只會淡化,不會消失
在我治療的一千多例癌症病人當中,最棘手的狀況,永遠是病人即將離去之前,悲傷而無法面對的家屬。那每每讓我想到《尋找失樂園》(Finding Neverland)故事裡,一位稚齡的小兒子含淚問出:「Why they must die?」(為什麼我的父母要死掉?)每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屬,似乎都以他們傷心的眼神,對我提出這樣的詢問。
我的病人林太太的小兒子,便是其中一個。
林太太是卵巢癌患者,和許多這類疾病的患者一樣,雖沒有明顯症狀,但一被診斷就已是第三期。經由手術後,再配合六次化療,林太太的小兒子卻希望母親轉而嘗試另類醫療。
同樣,很快地,林太太的癌症復發了,再回到醫院來時,已有廣泛的腹腔散布和內膜積水。並且因為腫瘤的壓迫,又瀕臨直腸阻塞,林太太本身不願意再接受手術治療,但只做了一次化療,嚴重的骨髓抑制就併發了敗血症,病況危急。
意識很清楚的林太太,有許多次表達希望平靜離去,她與丈夫也早已簽署了〈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〉。
當初要林太太做另類療法的小兒子幾近崩潰,他不願意就此放手,因為他深感愧疚,覺得都是因為自己要媽媽不再接受西醫治療而去吃中藥,才害死了媽媽。他一再地苦求醫護人員千萬不可以放棄對媽媽的積極治療,幾次情緒失控。
有天下午,我就這樣抱著這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大孩子,我安慰著他,不是以一個醫師的身分,而是以一個同樣經歷喪親之慟的人子角色。我對他說,十七年前,在我最景仰的父親去世前,我也是何等的不捨,但為了讓父親放心離開,我在父親臨終之前,對他做了什麼承諾與如何道別。
我告訴這個孩子:「你該趁著媽媽神智還清醒,告訴她,你愛她,並且會永遠記得她;請你告訴她,你會照顧你年老的父親,請媽媽不用擔心;也請你告訴她你會努力上進,好好生活,珍惜她給你的人生,也讓人因為你而紀念她。當時,我就是這麼告訴我的父親。」
我想,這孩子接受了我的建議,最後順從了媽媽的心願,讓媽媽平靜而去。但我至今還在等待當時他跟我的約定──他說,辦完了母親的後事會再與我聯絡,讓我們分擔彼此的憂傷。
我知道,失去親人的哀傷會隨著時間淡化,但是卻從來不會消失。
在痛苦的試煉中反思
之後,我參加馬偕醫院精神科方俊凱醫師的一項研究計畫:「以照顧癌末病人之醫學倫理,建構醫師靈性成長課程」,引導我具體審視自己行醫生涯的成長經驗,並進一步了解自己身為醫師的深層意義。是的,就像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說:「我們偶爾能治癒疾病,經常可以解除痛苦,但永遠可以給予安慰。」
遇到醫療的困境時,有些醫師可能選擇只扮演有限的身體醫治的角色,抽離情感;有些人則期待隨著時間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。然而,使人成長的不是時間,是用心、是投入,是痛苦試煉後的反思。
經過這樣的過程,一名醫者可以從技術層面的追求,昇華為對全人的關懷;從無力的嘆息,轉變為超越知識和制度障礙的努力,而能夠給所愛的人不拘形式的靈性關懷,就像遠藤周作的小說《深河》中,那位背負著印度教教徒,到恆河中去做臨死前洗滌的天主教神父。
(本文摘自《在我離去之前:從醫師到病人,我的十字架》,寶瓶出版,楊育正, 楊惠君著)